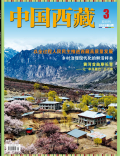50年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家长奴隶制阶段的珞巴族,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如今,他们呈现出与中国其他地方人们一样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珞巴人说,他们50年来的变迁,相当于人类社会2000年的发展。
小洋楼取代了茅草房
山顶白雪皑皑,寒气袭人;河谷鲜花盛开,绿树成荫。
8月下旬,记者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深沟窄涧中的米林县南伊珞巴乡采访时,每到一个村落,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抬眼望,山顶白雪与浓雾结伴萦回;侧耳听,阵阵松涛中夹杂着鸡鸣狗叫声;漫步行,河谷平野里三五一群的牛马在明媚阳光下悠闲吃草。在此世外桃源般的景观里,幢幢居民藏式小楼掩映其中,门前的农机具闪着金属的光泽。
来到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村,推开松柏坡下一幢藏式彩绘楼宇的铁皮大门,三围方石院墙中间的石板甬道直通楼门,甬道两侧是碧绿的草坪。楼上楼下共约500多平方米的房内,铺有釉面地砖、挂石膏顶棚。楼下是粮仓,楼上东为卧室,中为客厅,西为厨房。屋里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话一应具全。这是达登老人刚住进不久的新房。
在四围摆满镂花木雕家具的客厅里,72岁的达登老人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年轻时,我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要不是国家政策好,哪有我今天的生活。”他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他们过的还是原始人的生活。他和老婆住在七根椽子支起来的茅草房里,晚上靠松香照明。上身披挂兽皮,下身什么也不穿,连鞋都没有。常年除了打猎,就是“刀耕火种”种一点青稞和鸡爪谷,肚子总是半饥半饱。后来,政府帮他盖了一间木板房,近年来,柏油马路修进山沟来,两个儿子买了汽车跑运输,家境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又盖了新房。“不过,像我这样的家庭在全村30户人家里也只能算中等偏上一点儿水平。”说着,老人发出爽朗的笑声,并让女儿打开组合音响和房顶的旋转彩灯让我们欣赏。
我们在这个乡了解到,高压电线村连村,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家用电器十分普及,八成以上的家庭盖起了新房,全乡85户人家中的17户买了大汽车、35户还装了程控电话,孩子们都免费走进乡完小学习。
乡长达久说:“尽管地处边疆,尽管我们人口稀少,但党和政府时时牵挂着我们。尤其是近三年实施的‘兴边富民’政策,国家投资490多万元,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通了路、电、自来水、广播、电视、电话,更是让我们向现代化生活迈进了一大步。”
达久说,2000年国家“封山育林”政策出台前,人们主要靠砍伐木柴赚钱,全乡年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现在人们响应政府号召跑运输、做生意、种庄稼和发展家庭养殖业,这两年人均收入保持在2300多元左右,比全区平均水平高出600多元,在所属的米林县处于中上等水平。目前,上级政府正在扶持他们开发旅游业、种植经济林、发展药材产业和旅游业,前景很乐观。他说:“以前人们说我们这里是‘桃花源’的时候,除了风景美丽的因素外,还包含着贫穷落后的意思,如今我们这里可是景美人富的现代‘桃花源’了。”
畜禽不再为祭祀而养
“珞巴人也卖牲畜?这可是新鲜事!”南伊珞巴民族乡才召村的达吉家,一次性卖了两头牛三只猪后,远在400公里外的拉萨人感到惊奇。然而,事实确实如此,珞巴族群众的经济头脑、市场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以前专为祭祀而养的家畜,如今开始走向市场。
也难怪人们的疑问,因为原先珞巴族群众家的牛、猪、鸡都是专为祭祀而养,从不出售。今年83岁的巫师达崩说,珞巴人崇拜鬼神,凡遇大病小灾、出行打猎、盖房种地等,总要请巫师占卜、做法、杀牲祭奠鬼神。占卜时,一般首先杀鸡看肝脏纹路进行释疑,然后宰杀大牲畜敬神免灾。因鸡肝颜色和纹路各有差异,释疑往往须同时看三四只鸡肝,才能算出所要敬供的神灵是哪一位、需杀多少牛和猪。杀猪宰牛后,也要观其肝脏,看神灵是否满意,若不满意,再接着杀鸡占卜,继续杀牲敬献。
乡长达久说,以前人们搞一次祭祀活动得杀不少畜禽,有的人家杀光了自家畜禽,或认为自家牲畜的毛色、相貌不吉利,就要向别人借或用物品换。而且,按照习俗,每次所杀畜禽肉都要在主人家里大宴一顿村人后,把剩余部分全都无偿分给村人。有人甚至因一次祭祀而倾家荡产。因此,别看珞巴族群众家家都有很多畜禽,但过去几乎没有经济效益。现在人们的见识广了,自然信鬼神的人就少了,方圆30公里内的巫师人数也从20年前十几个锐减到现在的2个,而且年龄最小的也70多岁,近10多年来没出现后继者。
乡长达久说,现在祭祀杀牲浪费现象一年比一年少了,多数人家还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生病就去医院看。前几年,全乡群众每年祭祀杀牛还能上好几百头,这两年顶多也就是十几头。今年,全乡牲畜存栏数为1772头只,出栏数301头只,出栏数是去年的一倍还多。现在各村正在筹划饲养商品育肥牛和猪。
青年男女旧“公房”如今有了新用场
昔日,在珞巴族聚居地,只要有不同部落或外民族人的村落,就都会有男女两座“公房”。据老人们讲,小伙子们的公房称为“邦哥”,姑娘们的公房叫做“雅胜”,均由全村人共同修建。公房一般设在村子中间,它与一般住房相似,不同的是比较狭长,开有多个小门。晚上,村里未婚青年都在各自的公房中居住,并接受专门选派的年长者口头进行的各种教育。同时,它也是青年男女自由接触、恋爱的场所。
如今的公房不分邦哥和雅胜,每个村子就一座,都是近几年国家投资,拆掉原来公房重新修建的,门口都挂有“文化室”牌匾,只是人们还习惯性地称它为公房。新公房比过去的竹竿、木板公房讲究了许多,全是用方石与上好的原木建造而成,它更像一个大教室,装修得较讲究,不设床位,大多摆有几架书籍,还有电视机、音响、VCD机、棋牌,有的公房还装有跳舞用的彩灯、电子琴等设备。
南伊乡才召村的公房,是政府投资10万元修建的。村民亚毕说,现在的公房有了新用途。因为青少年都由政府“包吃、包住、包学”,走进正规学校,接触外面的机会也多了,就没有必要再住公房了。“现代公房”由村委会管理,经常开办群众扫盲班,开展果树、蔬菜栽培、家庭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孩子们假期回来可以在这里学习、娱乐。
1983年毕业于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乡长达久说:“西藏和平解放前,我的父辈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珞巴族一下子从原始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又经过50多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优惠扶持政策,我们过上与全国其他地方人们一样的现代生活,可以说我们珞巴族的变迁,等于人类社会2000年的发展。”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珞巴人通晓藏语和汉语,珞巴族公民在西藏自治区各级单位工作的干部就有30多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有珞巴族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