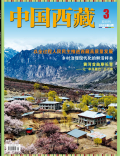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牧区,这就意味着西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公益设施以及医疗、教育等都全部或部分地依赖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完善村级组织、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效能对西藏广大农牧民的现实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我们把村级组织视为最底层的“政府”,还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总之他们所有的公共服务活动中任何必须的经济开支都来自于村民,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即便如此,我们的调查显示,西藏村级组织在完成上级政府委派的诸多任务的同时①,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有效的公共服务。
协调农业生产
对于像西藏这样依然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村来讲,组织村民协调有序地利用农用资源,依然是村干部的首要任务。为此,一般地,县里要组织村干部就有关农业气候、农业知识及相关政策等进行集中培训。对村干部来说,农业生产中的难点集中在以下三点:春耕、秋收与用水。
统一春耕不仅可以避免由于春耕先后造成牲畜践踏等引起的纠纷,更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因为在春耕时要举行特别的开耕仪式,这一天的选定要经过村干部和村里的老人们共同商量,根据天气、树叶等自然现象以及宗教上的吉日以确定开耕日期。村民们认为这既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也是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做法。秋收的统一除了避免同样的纠纷之外,也有一些宗教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随意地开割可能导致雹灾等恶果,因此,也要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才能收割,并且多数的村庄都规定,先收集体农田,然后才收割自家农田。而用水对于所有的村庄来说永远都是矛盾之源,值得村干部动用传统习惯、村规民约以及干部权威等全部的权力资源来维持有序的利用。
在个别案例中,我们还看到村干部为村民提供的农业服务范围更为广泛,比如在康来村,村长还负责选种,将选好的青稞、油菜种子,在村内进行交换、分配。
维护治安秩序,调节民间纠纷
维护治安秩序,调节民间纠纷作为村级组织的职责之一,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具体操作分为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采用层层签订社会治安责任协议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户网络进一个组织化的治安防范体系之中②。在微观层面上,对于村庄中的突发事件或民间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村干部的调解和仲裁一般来说都以村规民约为依据,但是,我们在调查中所见到的村规民约大多内容相仿,实质上已经过政府的改造,成为体现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原则的通俗版本。由于它未能充分反映地方性传统,因此村干部在实际操作中还不得不援引当地传统、习惯法等,而村干部年轻化所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传统的调解和仲裁手段的陌生,因此往往要请老人权威参加。但是无论如何,在经过国家行政建设的多年努力后,西藏历史上共同承担纠纷仲裁职能的寺院活佛等已经淡出村庄治理的舞台,以村干部为主导,由老人权威提供协助成为一种常见的模式。
村民纠纷案例1——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边给村
边给村村长次仁坚赞介绍村里的治安状况时说。村里专门设有纠纷调解委员会,村长任组长,副村长任治保主任。在他任村长16年来,村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刑事案件。请上级政府来调解的也只有二三件。但是小纠纷还是经常出现。比如3年前,在给田地浇水时,有一户村民不按顺序灌溉,擅自放水,其他村民有意见,于是闹起来,由于不服从调解,他只好请乡书记来调解,公开批评了那户村民。这一家心存仇怨,至今不跟他说话。
村民纠纷案例2——拉孜县拉孜镇康来村
康来村村长旺朵介绍村民纠纷时说,总体上需要他调解的纠纷并不多。关于处理纠纷的办法村里有具体规定:如果发生口角,罚款10元;打架出血,罚款30—40元;所有的罚没款都归村里开支。最近他处理了一件家庭纠纷,村里有弟兄二人为各立门户分割家庭财产出现纠纷,于是旺朵和几位老人前往调解,他们把家里的东西估价分成二份,编号后由弟兄两人抽签决定,这样大家都觉得公平。
主持村庄公益项目
村庄公益是一个内容极宽泛的概念,包括对村民日常生活条件、医疗卫生、儿童教育、救灾减灾等集体福利的改善。为村民提供公益产品是村干部作为村政领袖的责任。我们在七村的调查发现,当前西藏农村的公益项目包括两类:一是外力启动的公益项目,比如国家和内地各省在西藏农村的援助项目,这些项目有相应的资金投入。雪卡村的“小康村建设”项目以及由于措高湖旅游开发带动的巴河镇公路建设、生态保护等都属此类。但是,这种“输血”式的村庄公益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村庄发展的逻辑必然。二是利用村庄公共资源所进行的公益项目,这种公益项目的目的在于满足村民最低的生产生活需要,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村子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而对公益项目有着不同的要求。
村庄公益案例1——木坝村治水
工布江达县木坝村地处巴松河(brag-chu)上游,河水从村子中间湍流而过,藏东南多雨的气候使巴松河每到夏季便泛滥成灾,泥沙覆盖了河边的田地,河水在村子里肆意漫流,威胁着村民的屋宅,每到夏季水患就成为木坝村村民的心头之患。因此,筑坝治水、架桥修路成为木坝村每一届村干部的重要职责。每当洪水过后,村干部就要组织村民出义务工清理河道,重建河坝。每当大雨之时,村干部们便密切注视水情,以便及时抢堵。
村庄公益案例2——康来村防秋雹
地处西藏自治区中西部的拉孜县,全县平均海拔4010米,每到夏末秋初,拉孜谷地一带气候变化剧烈,雹灾频繁,常常造成农作物减收减产,防雹成为关系村民生计的一件大事,村干部为此必须竭尽全力。康来村的防雹有两个途径,一是用高炮(雹炮)打散雨云;二是用宗教手段,比如请防雹喇嘛(ser-ba lama)念经、做法。虽然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在看到雹炮防雹有效后,就不再请防雹喇嘛,但是康来村依然沿袭传统,村里轮流每年由一户村民请一位防雹喇嘛来念经,喇嘛做法需要的糌粑、牛奶等由各户村民共同筹集,那户负责邀请喇嘛的人家要负责给喇嘛的15元报酬以及他离村时布施的蔬菜等物品。
为村民与外界的交往提供中介服务
虽然市场经济对西藏农村的影响还处在初始阶段,农民的生产活动远未进入商品化阶段,但是,劳动力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已经开始,富裕劳动力的规模化转移已经出现。在农区七村,笔者了解到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到阿里、那曲等牧区从事建筑和鞣皮等工作。近年来国家提倡并资助牧民在冬草场修建定居房,但是牧民不善建筑,而农民则精于此道,因此,在夏季许多农民前往牧区给牧民盖定居房、筑畜圈以获得劳务报酬。前往牧区鞣皮也是西藏农民一项古老的增收途径③,但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被禁止。二是参加政府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其转移范围远近不等,最远的前往藏北参加青藏铁路工程的建设。三是转移到城市,从事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近年来随着中央及全国各省市援藏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因此富裕劳动力的转移被各级政府视为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为富裕劳动力寻找转移门路,就成为村干部的重要职责。
对外交往案例——查武村的富裕劳动力转移
倡导和组织富裕劳动力转移是日喀则地区确定的农民增收的政策之一,要求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全力贯彻。查武村也为此积极努力,2003年全村劳动力转移总数达到150人,其中许多人是自己寻找门路外出打工。但是,仍有许多村民没有出去打工的门路,需要村干部为其寻找。村长欧珠说他们一般有两种办法:1,平时与一些包工头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工程开始施工时,动用这种关系推荐本村村民加入施工队。2,如果包工头是本村人,村长的推荐则更具效力,欧珠说,该村有三个包工头,他就要求他们必须首先雇佣本村的劳力。所有这些中介服务都是义务的,村里不收任何费用。此外,还有7个人由县里联系并组织前往青藏铁路工程参加施工劳动。
促进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参与市场竞争
青稞、油菜是西藏传统的农作物品种,但是这些农产品附加值小,难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为调整农业结构,逐步适应市场经济,政府提倡农民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引种新的经济作物。但是,对于个体化的农户来说试种和参与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规避风险的理性使村民大都采取观望的态度。在结巴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针对上述情况,利用村里的公共资源进行实验、示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案例——结巴村利用公共资源为村民进行商品经济示范
结巴村位于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北约18公里处。虽然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市场便利,但前几年村民对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心存观望。后来村干部决定利用村集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示范,以促进村民观念的转变。为此,村集体先在公田里种植土豆、蔬菜等经济作物,获得市场成功后,又开办了养殖短期育肥羊、藏鸡养殖场、喂养奶牛等多个项目。集体的85亩果园,通过承包方式经营良好。2002年结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5万元(笔者根据各项目的收入估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减轻了村民的负担,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和村民的“统筹”都由村集体收入中支出,贫困户的救济和重病病人的药费也适当地从集体收入中给予补贴(这一项在2002支出了4000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看到了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发家致富的途径和方法,许多农户参照村集体的经营方法发展个体经济,同样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如今整个结巴村已成为乃东县“庭院经济”示范村。
结巴村利用公共资源参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力地回击了长期以来关于西藏农牧民是否有能力参与市场的怀疑,还使我们看到,西藏传统文化的道德约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面。集体经济通过个体承包的方式经营在目前是常见的方法,但是这一模式在内地农村多数以失败告终,个体经济对于集体资源的侵吞无法避免④。而在结巴村承包制却能运转良好,这不仅因为村委会制定了良好的规则,还因为有传统文化的道德约束,村民对集体经济的随意破坏以及违法侵吞(比如偷盗等)极少发生。结巴村的事实也使我们看到只要确立良好的规则,村级组织可以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为村民参与市场起到推动和示范的作用。
利用民间权威,塑造村庄整体观念和凝聚力
自从70年代末国家逐步放松对农村的控制以来,许多民间权威在西藏农村逐步活跃起来。首先是宗教权威如活佛、堪布、僧人以及民间神职人员借村民宗教信仰复兴之力,依照古老的传统出面组织、主持各类宗教活动,成为村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宗教权威案例——还俗僧人阿爸次仁
68岁的还俗僧人阿爸次仁因为具有丰富的宗教知识而成为雪卡村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物。阿爸次仁祖籍青海玉树州囊谦县,自小出家为僧,属于竹巴噶举(’brug-ba bka’-brgyud)派下竹巴(smad-‘brug)系统。1951年18岁时到西藏朝佛转经,恰逢当年玉树州解放,他听说家乡局势动荡,无法回去,就留在雪卡村,并于1958年结婚成家。据阿爸次仁回忆,“文革”中间不许搞宗教活动,他也不再念经。1972年宗教政策有所松动,开始有了一些宗教活动,以后就逐渐恢复了。一般来说,村民遇到以下情况会请他念经做法:1,家里有人得病,请他念平安经,或祛除鬼魔。2,家里有人去世,请他念经超度。3,村民家里要盖新房,请他念经镇魔消灾。此外,村里许多集体性的宗教活动也由他组织和主持,比如:春天的开耕仪式、初秋季节的望果节、以及祭拜“扎日公宝(brag-ri mgon-bo)”神山等。
其次,传统的回归,使老人们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了特别的价值,特别是政府在乡村权力的回撤,使村干部需要自主地处理村务,这使得村干部个人的人生阅历和人格魅力就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干部年轻化原则下产生的村干部显然于此有所欠缺,于是老人权威便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当前西藏农村的民间权威已与他们在西藏历史上所具有的强大影响无可比拟,他们对村级组织的权威已无法构成实质威胁。相反其中的多数所具有的村民身份决定了他们自己的福利还要依靠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现在他们已经常成为村级组织需要时可资利用的权力资源。由于他们对村庄凝聚和整体观念的塑造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村干部也乐于看到他们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在西藏看到一些村庄集体性的宗教或娱乐活动如望果节、转神山等常常是村干部和民间权威共同出面主持的原因。
①政府为了避免村级组织对其目标的消极态度,普遍地采用责任协议书等强制形式加以约束.笔者在乃东县结巴乡就见到了有关农牧民增收指标,森林防火,社会治安.预防鼠疫,防止"非典",妇女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以及青年工作等8种责任协议书.
②参见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③(美)梅尔文·C·戈尔斯坦、辛西娅·M·比尔著,肃文译《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3页。
④参见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