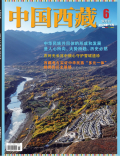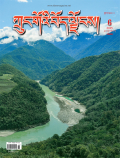每一个踏上通麦天险的人,无不心怀敬畏,这段八一与波密之间的路程共14公里,沿途山体脆弱,河流密布,一旦风雨交加,就可能引发泥石流,让这条路被称为“死亡路段”。不管是修建川藏线通麦路段还是维护该路段,都有英雄长眠于此。
但以旅人的角度来看,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一侧山峦高耸,连绵不绝,山体植被茂密,云雾缭绕其间;另一侧则是奔腾不息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像一条灵动的丝带穿梭在山水之间。如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G318线波密至鲁朗段改扩建工程已经完工,波密县通麦镇的项目部也已撤去,路面变得更加平整顺滑,帕隆藏布似乎也变得更加温存,路边的防护栏等设施修葺一新,为行车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厨师陈双才,便是项目部的一员。2001年,陈双才听从父亲——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教诲进藏,亲身经历了西藏二十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故事便从他入藏时讲起……
五道岗
陈双才拎着行李站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砂石路上,大口地喘着气,似乎天地间只有他一个活物,藏羚羊呢,藏野驴呢,雪豹呢,牦牛呢,都没见几只。十几个小时,窗外只有灰色的天和山脉,车两侧黄绿相间的斑驳草地不停变换。风掺杂着沙砾劈头盖脸地扑来,旁边一家补胎店门口的铁皮呼啦作响,泥土搭建的店铺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陈双才不得不侧过身好让自己呼吸顺畅。
“要折返,你起码到五道梁,再说,翻过唐古拉山,那可好多喽,万里长征剩几百里,你要当逃兵嗦!”同行的乘客下车劝他。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催促,他刚同意了陈双才下车的请求,路旁的补胎店有方便面火腿肠,可以歇脚。这位爱嘟囔的乘客可以在这等到回格尔木的班车,至于要多久,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跟车的青海小伙下了车,吼道:“到底走不走!”陈双才还是头疼,却突然冷静了下来,从他家那个叫三合堰的小村子带着几十斤行李,坐三蹦子到市里、火车到西宁、大巴车离开格尔木、过了西大滩、到昆仑山口,几千公里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咬咬牙,把帆布包和蛇皮袋重新塞回车里——“忍一哈,坚持一哈,莫要拉稀摆带!”陈双才给自己打气,重新爬回了各种气味混杂的车厢。
车子一溜烟没入了云端。司机和乘客闲聊:“‘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五道梁都过了,再下唐古拉山就好多了。”陈双才忍住剧烈的头痛,想分散下注意力,他打听藏羚羊去哪了,是不是让偷猎分子捕杀了。
“他们(指偷猎藏羚羊的不法分子)都进去了,羊子有哩,等一会儿。”司机灌了口茶。
不一会儿,陈双才看到了藏羚羊。接着,藏野驴、成群的牦牛、晶莹剔透的流水似乎商量好地接踵而至,陈双才觉得清醒了许多,在沱沱河堵车时甚至下车抽了根烟。
“当时对西藏心里还是有一种恐惧感,有点怕,路上一瓶矿泉水至少要十元,有的地方更贵,我买了几个他们叫撒子‘焪锅’的大馍,喝一口水,吃一口馍,馍带到拉萨吃了几天才吃完。”
“坚持一哈嘛。”陈双才习惯性地往围裙上抹了抹手。
陈双才1966年出生,属马,身形削瘦,说话时专注地看着我,仿佛往人心里灌输一种无声但坚韧的力量。他第一次进藏时,儿子陈虎在四川崇州市公议乡三合堰村上五年级,第二年陈虎的母亲也动身前往拉萨。
啤酒之争
起初,“西藏新人”陈双才是来做酒水生意的。当时拉萨销量最好的是黄河啤酒,这些啤酒从青藏线运来,再装到人力三轮车摞个几十箱送往拉萨各个店铺、小卖部,货运站常常呈现出一幅游击队四处出击的场面。拉萨啤酒在迎头赶上,雪花啤酒铺天盖地的营销广告也是山雨欲来,至于市中心的酒吧、朗玛厅,则是百威和嘉士伯的地盘。
“黄河啤酒粗犷一点,有一点酸,不是很苦,入口后会再回甘,生津。像是在沙漠中渴了好久喝的第一口水,很独特,这是西北的风格,但满大街的火锅店、川菜馆越开越多,运费人工都涨,‘黄河’不行喽,我们重庆山城啤酒度数低点,清爽、巴适,我打算分一杯羹。”
“啤酒买卖是一个具有消费惯性、大品牌垄断、当地品牌也深度参与的生意,外来品牌初次进入打开市场十分不易,重庆啤酒靠的是老乡人脉。”
陈双才一共做了七年的酒水渠道供货商。开始时各处跑,从酒吧、小店到烧烤摊,和服务员数啤酒盖算钱,下午晚上守在饭馆门前等着给老板推销重庆啤酒。
“小区里的超市好一些,顾客比较稳定,老板进我的啤酒价格更低,要么进够多少就送东西、降价,只要进去就能逐渐加大我的出货量和陈列量。”
“再一个,有些歪的招。比如,有的人和收废品的谈,只收他的瓶瓶儿,别的不管。只要钱到位,满足了收废品利益需求,结果就是,别家的空瓶瓶儿没人收,夏天一放,那味道相当难闻,而且占地方,你说老板撒子心情。”
“歪招还不少,我没这样干过哈,因为不是长久之计,但你做这行要晓得嘛,免得着了别人的道。”陈双才说。
靠着积攒的口碑和人脉,陈双才赚了一些钱,后来也做过白酒,但问题随之而来,铺货量越来越大,需要自己垫付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有次轻信于人,合作伙伴信誓旦旦让陈双才第二天去结货款,结果等他去时却已经人去楼空。
“生意起伏不定,那段时间经常失眠。”陈双才说道。
“最牵心的还是娃儿。”陈虎渐渐长大,别的父母对孩子守护陪伴,劳心劳力,陈双才夫妻二人家长会一次未参加不说,就连儿子中考也不在他身边,最长的一次甚至和儿子三年未见。陈双才听到的一个词:“叛逆期”,这让他心绪不宁。
“陈虎学坏了怎么办?”陈双才更睡不着了。
“我五年级时,父母便去了拉萨,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过年。一年甚至几年不见父母,似乎已经习惯了,见到时反而没那么激动。”陈虎说。
“小姨和姨夫也在西藏务工,他们每年过年会回来,分开时表弟痛哭流涕,把充电器什么的藏起来,阻止他们离开,我觉得很幼稚。”陈虎有点腼腆地说。
陈虎初中毕业时,他想来西藏看父母,青藏线路上时间长,陈双才不放心,警告陈虎不要独自前来。陈虎便去打工,发传单、卖竹笋,人生中第一次挣到了钱,给父母买了四双鞋寄到了西藏。陈双才听着电话那头,儿子讲老板怎么骂他,心如刀割。
2008年春节,陈双才夫妻二人回家过年,本打算过完年之后返藏清一清生意账目。然而春节后,喧嚣褪去,陈双才审视着长大了不少的儿子,这时陈虎即将从怀远镇重点高中毕业,每晚学习到深夜,做高考前最后的冲刺。陈双才决定暂缓入藏,陪儿子一起准备参加高考。
天路烹饪
2006年,陈虎读高一,青藏铁路开通了。暑假,陈虎从成都坐火车到拉萨,近五十个小时的硬座,陈虎脚都肿了。一下火车,母亲便将他接回家,一家三口终于在拉萨团聚了。
陈双才坚持自己动手做饭。不忙的时候,家里就是陈双才主厨,他做的饭菜在老乡、朋友圈小有名气,何况这是儿子第一次来拉萨。陈双才捞出卤好的鸭掌、猪耳朵、肘子等,取出发好的鱿鱼和当时拉萨市面少见的海参,便开始忙碌起来。出租房充满炒豆瓣酱的香味,小圆桌上摆满了各色碗碟,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了在拉萨的第一顿团圆饭。
陈虎开心地说道:“能天天吃到爸爸做的饭就好了。”
三年后,陈虎考入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陈双才如释重负,决定放弃酒水生意,从事自己一直喜欢的厨师行业。
2009年,陈双才经朋友介绍来到了G317线夏曲卡至那曲公路整治改建工程B标项目部,负责三十多人的伙食。
在这里,陈双才感受到:这里似乎没有空气的存在,天蓝得让人心颤,纵横交错的溪水下草根晃动、泥土清晰可见,光线一直透到水底。尼玛县孔玛乡,海拔4580米,比拉萨高一千米左右,水烧开只需要八十多度,他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
陈双才刚到便参与了一场小规模救援行动。“刚去的那天天气是假象,第二天下午沥青拌合站的帐篷就让大雪压塌了,我就晓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项目部的人七手八脚掀开帐篷一角,把埋着的人一个个拉出来,大家大口喘着粗气,嘴唇都是青紫色的。
“要稳扎稳打,最重要的是保证干净的水、燃料和食材。”陈双才每天和徒弟们开一辆锈迹斑斑的皮卡,车厢里放着三个大铁桶,去十几里外一条稍宽的溪流拉水。冬天把冰面凿开,捞起透亮的冰块,有半尺厚。
“物资就是这么短缺,带盖的塑料桶都没得,拉回来的水洒一半,再沉淀一夜,第二天才能用。”
陈双才又修整了一架不知道哪来的小推车,找人焊接一番,一有空就去捡牛粪,因为不知道哪天会大雪封路,气罐车有时走到一半只有折返回去,液化气很难保证稳定供给。
“草原你看起来是平的,其实都是一个鼓包一个鼓包的,大包接小包,车子在上面过山车一样,我的小推车也和皮卡车拉水一样,不能太满,要不牛粪都洒喽。”
谈起厨师工作,陈双才如数家珍。
“做菜嘛,要保证卫生,营养和口感,不像大饭店里那么精致卖相好,但吃得一定要卫生、舒服。”
陈双才说,那曲鼠害较重,老鼠不仅侵蚀草场,有的甚至在人的眼皮下大肆啃食食材,有时进门,一跺脚,就有老鼠四下逃窜。
“食堂肯定是重灾区,但我后来采取了一些办法还是管用的。”
起初,陈双才用木架把食材架起来,将四个脚撑抹上黄油并放进水桶里,设想中老鼠不仅爬不上去,还会一呲溜掉进水桶。但老鼠能“上天入地”,陈双才有次看见老鼠在桶里游了个泳,沾点水蹭着黄油继续往上爬。
后来,陈双才托人从拉萨带回来了一种细钢砂网,不锈钢制成,价格不菲,四块勾连焊接在一起掏出小门,组成一个小型的钢笼,把食材装进去架起来,从而隔绝了鼠害。
“菜品质量也要稳定,不能由着性子来,比如你今天心情好,精雕细琢一大桌,哪天又胡搞一番,这样大家就会有意见。说实话,在那个地方,睡觉都不一定睡得好,一天最大的享受便是吃饭。”
慢慢地,陈双才学会了辨别虫草,偶然得到一两根,放进稀饭里。项目部的人围观虫草稀饭,都惊讶不已。
三代传承
陈双才问,流动党员是什么意思,在哪交党费,现在入党需要什么流程等。原来陈双才的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以前做过三合堰村大队长,生前就鼓励陈双才到西藏去,希望他扎根高原边陲干出一番成绩。在那曲的第三年,老父亲病危,陈双才连忙请假,回去守在床前一个月尽孝直至送终。
2021年,儿子陈虎也加入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在西藏天路(林芝)代建办,负责工程项目的前置手续。
“以后能天天吃到爸爸做的饭就好了。”多年后,陈虎如愿以偿。但是,2018年就已入藏工作的他还是和陈双才聚少离多,这也是工程人的常态。
但是,陈虎说:“再也不用像第一次来拉萨,分别时在站台强忍泪水。那时,火车启动后,转头看车窗外,父母在抹眼泪,却越来越远,只听见车厢里嘈杂的声音,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2024年8月19日傍晚,海拔2200米左右的西藏林芝通麦镇,曾经的藏建·天路波鲁项目部的工程已经完工。在茫茫雪山和绿色山林环绕下,新修的公路像一条丝带蜿蜒,陈双才故地重游,在视频里逗弄着刚上小学的孙儿。他说,现在家里是四世同堂,视频里几个老太太搓着麻将,精神矍铄,看着喜庆极了。
“川藏铁路一通,相关公路配套设施完善,回家只要几个小时。”
“陈虎他们现在吃点苦,难一点,修好了不得用上几百年。”
陈双才平时话不多,今天也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
陈虎说,这里就是家。此心安处是吾乡,“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不仅仅是一句标语,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们通宵达旦、热火朝天的真实写照。身处举世瞩目的“世界屋脊”,西藏的发展天翻地覆,面貌改天换地,人民生活今非昔比,实现了跨越上千年的沧桑巨变。如今的西藏,原野千里,处处生机勃勃;高山大川,一派欣欣向荣。
这离不开陈双才父子这样的普通建设者的辛勤付出,他们二十多年的经历,无不表露着一种中华民族的共性——坚韧、感恩和积极乐观的奋斗精神:拿起厨具(热爱的事业)便是生路;遇到挫折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迎难而上想办法克服;在工作生活中与当地百姓交往交流交融;为了子女的教育成长付出辛劳;孩子长大后也义无反顾进藏……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口音,奔波扎根于西藏,以实际行动汇聚成建设西藏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