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三位故友
文·图/班丹
进入21世纪之初,我相继失去了赤来加措、达瓦次仁和加央西热三位老师级朋友。他们三位都是读书做学问、著书立说的人,在西藏文学艺术界颇有名气和影响。特别是加央西热以长篇纪实散文《西藏最后的驮队》问鼎“鲁迅文学奖”,为沉寂多年的西藏文坛争得了荣誉,唤醒了一拨矢志不渝为西藏文学的振兴而孜孜以求,却疏于文学自觉意识、自身素养和客观因素而未找到有效出路的文艺界人士。

◎赤来加措。
赤来加措为西藏翻译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赤来加措年长我十一、二岁,我管他叫觉赤来啦——赤来大哥。这是我对他的一种亲热的尊称。
我对赤来大哥的过去可谓一无所知。只是性情豪爽、耿直的他,把他不为别人所知的一些事情断断续续地讲给我听过。所以,我知道他曾喂过猪,养过鸡,当过民工,干过木工活,插过队,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供过职。他生前的确切身份很难确定,但就长期从事的工作及其主要成果而论,说他是翻译家大致错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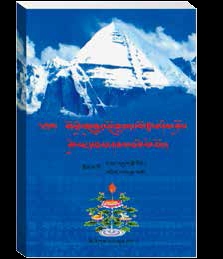
◎赤来加措著作(与人合著)。
我跟他共事七八年。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成熟、乐观、真诚、厚道,有浓厚的生活情趣。他堪称是一位天生的语言大师,有语言天赋,像功底深厚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说话总是那么幽默、诙谐、风趣而又不失生动形象。他善于讲笑话,编顺口溜,给人送雅号(从不给人起带有侮辱性的外号),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且富于文化底蕴和内涵,张嘴就来,脱口而出。曾有段时间,我们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翻译室为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半月谈》承担部分文稿的翻译任务,其稿酬在当时不算高,每千字只有二十余元人民币,平均每人每月一百来块钱。那时,恰巧他也吸点烟。当时我们吸的是二十一元一条的画苑牌香烟,用那点稿酬买几条画苑牌香烟绰绰有余。一天,我们在办公室正忙不迭地翻译一个急件。当大家都感觉又累又着急的时候,他停下笔,递给我一根烟,他自己不紧不慢地点上一根,悠然地吸着,环视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腾地一下站起身,冒出几句快板式的顺口溜来:“《半月谈》里出画苑,抽起画苑精神爽……”只要与他在一起,你就不愁听不到有趣的事情和笑话,常常逗得我们几个同事笑得合不拢嘴,伴着朗朗的笑声完成工作任务,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滑过去。
一次我问他,您说话总是这么风趣,是怎么练就的?他微微一笑,不假思索道:是在东嘎插队时吃蚂蚁吃成的。原来他在农村插队时,在一个月夜与同伴一起去浇地,浇地间隙煮了一锅帕土(面疙瘩)。在做面疙瘩时,他们

